時間:2014年7月
地點:香港活化廳
受訪者:李俊峰(香港活化廳主持人)
訪問者:黃孫權
活化廳是一個由十多位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共同營運的藝術組織,期望以持續性的對話建立一個「藝術/社區」彼此活化的平台。置身於上海街,一個充滿本土特色卻又面對變遷的社區,「活化廳」期望試驗一種建立在生活關係的「社區/藝術」,並藉著不同主題的藝術計劃,引起人們對藝術/生活/社區/政治/文化的思考和討論,亦藉以打通社區豐富的人情脈絡,帶動彼此的參與、分享和發現,勾勒一小社區鄰里生活模式可能。
黃孫權:阿峰,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你的背景,你的所學,以及為什麼會來到活化廳?
阿峰:我2007年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本來是藝術家。2009年的時候我們開始在這裡營運活化廳。這個空間是1999年開始,在油麻地其實有一段時間了。最初是因為藝術發展局想要在這裡做社區藝術,一個藝術家叫秦江偉,是他發現這個地方,覺得可以用來討論社區藝術、定義社區藝術,所以就找了十個藝術家,我們就在這裡展開不同的計劃。在油麻地這個老區,面對發展的威脅,特別是地產商跟政府常常很想用藝術作為社區發展或重建改頭換面的工具,我們開始去想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藝術在社區裡面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角色,比如用藝術跟街坊建立一種關係,在這個發展裡面搭出另外一種可能性。因為按照文化廳的意思,就是政府跟地產商要重建一個文化社區,其實只是聽起來比較好聽而已。而我們期望實驗一方面是帶出新可能性,另外一方面想追問藝術文化社區這裡面的意思是什麼,簡單說就是怎樣可以增進文化跟社區的關係。
黃孫權:你可以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活化廳組織跟運作的方式麼?
阿峰:活化廳早期是比較藝術家集體操作,大家都是平等的,定期會開會,開會的時候討論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去做。平常我們有兩個職員在這邊,街坊也會幫手。後來就慢慢演變,越來越多街坊的參加,慢慢地有序地發生,沒有一個很嚴謹的組織。其實是用個體來做單位,比如說有些藝術家想要發動一些計畫,就變成為一組藝術家跟一組街坊的組織,就變成大家一起自發地去搞。
黃孫權:活化廳的運作方式是否可以算是一個獨立媒體?
阿峰:對,因為活化廳本來的定位是它想要參與、提出一些東西,然後讓大家去改變一些想法。比如說西九文化區,它給大家的想像就是我們在西九龍這個地方會有一個文化區,在裡面藝術跟生活的關係很接近,大家平常有空就會去看看,距離很近。活化廳其實在這個背景中間生化出來的,因為我們藝術家就在這裡,就會直接跟街坊有一個點對點的接觸。
為什麼說是媒體?因為本來活化廳的性質就是提出一些東西,藝術家有些案子、有些概念提出來,大家都覺得是很新穎,有一定的回響。最初在文化廳有一個想法,叫「街坊行動處」,是個什麼東西呢?因為我們固定在一個點,每天都會接觸到很多走過的街坊。比如說我們在這裡討論,有時候是明星,有時候會談地產霸權,會談租金價,會談有一些小店關門、傳統文化,也會談一些大的政治上的問題,比如說普選、六四,這些都會談。通過這些討論我們在實驗,怎樣用空間上的一個點來影響、聯繫到附近的街坊,然後看有沒有機會一起行動,看看碰撞到的附近社區有沒有什麼改變。比如說我們如果做六四的話,他們會不會跑進來罵我們,還是會走進來做什麼。比如說我們做一個獎杯的計畫〈多多獎 小小賞〉,藝術家就為一些街坊小店做獎杯,其實是一個雕塑的計畫。我們會邀請街坊去舉報他們的封關的歷史,藝術家就替你做一個獎杯這樣。所以這個空間就好像一個媒體,因為媒體就是可以聯合一些相近理念的人走到一起,讓這個本來隱形的意見可以凝固起來,再下一步就是建立到一個小群體的時候,大家都會有再進一步行動。
黃孫權:我知道你們好像出過很多社區刊物,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阿峰:《活化報》是活化廳搞了兩年之後才做的。2012年頭,其實是去東京看到素人之亂做的社區報,他們自己在A4紙上面畫的,就放在他的店外面,然後人走過就拿這樣,很輕鬆地就可以去做一個社區報,就可以輻射到附近的人。受到啓發,突然覺得我們也可以做的很輕鬆,不要想到做社區報是很難的東西,所以回來就做這個《活化報》。我們做《活化報》有三個定位,一個定位是它每一期有一個主題,主題就是找油麻地社區裡面的一些重要的議題,這些議題放大到整個香港可能是沒有人提的,但是在油麻地這個地方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會專題去報道。比如說攤販,比如說有一個在街上畫畫的爸爸,他在街上畫了四十年的人像畫,他的店被拆掉了,這個事情如果你放到整個香港,可能大家不會太留意,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小社區裡面談就很不一樣,因為大家四十年來每一天都看見他在街上畫畫,很慢很慢地畫,所以大家都會關注這個。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一些比較生活性的東西,因為香港一些獨立媒體,有一點小眾,所以我想要比較軟一點,就是街坊真的會看的。我們藝術家就會想很多有趣的專欄出來。比如說我們中秋節的時候有印發折價卷,他們剪下來可以拿來換一個月餅,有時候講附近的小店的食物,找街坊教煮一些菜,找一些南亞的小朋友畫畫,教大家南亞巴基斯坦的家鄉語言,就是比較軟性的的。還有一點就是活化廳做過的事情,外面的街坊可能不知道,因為他們平常開店看不到,也沒有空進來。但是我們《活化報》就變成好像活化廳的延展。因為我們印兩千份,一千份在這裡,一千份派到外面,然後我們會花一些時間,可能幾天的時間,就一份一份地投到他們家裡的信箱。所以附近的街坊只要他拿到這個也同樣會知道活化廳平常發生了什麼事情。
黃孫權:到現在出了幾期《活化報》?
阿峰:最後出了十五期,但是現在還在出,但是給藝術發展局製作之後停了一回,然後我們一個成員,就是Worlan(音),在我們停製作之後每一個月都會在街上擺地攤,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區報》,因為我們這個叫活化區。我們一大堆藝術家跟街坊朋友一起擺攤,然後也出一份報紙就講擺攤的文化跟小販的重要性,就是為什麼要用公共空間來做這些事情,關注擺攤的生態。
黃孫權:你怎麼想象一個藝術家團體跟社區之間的關係?
阿峰:藝術家跟社區的關係其實有很多面,藝術家常常有很多機會,就是把你放到一個社區裡面,跟外面的脈絡脫離,就好像我們最初可以空降到這個社區。但是有沒有想過其實在這個區藝術家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們,還是中間可以怎樣互相影響。可能到現在,街坊也沒有很理解藝術家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但是我們可能又跟他們一起生活了五年。當然,我覺得中間有些慢慢互相影響,就是我改變街坊的一點點東西,街坊也改變了我們一點點東西。當然首先你先不要覺得我帶一些東西給這個社區,其實你需要謙卑點,然後就是真的在這裡生活一段時間,先是一個街坊,然後才是一個藝術家。
「街坊」有點親切的味道,就是真的有一點聯繫的才會叫街坊,也不會叫「鄰居」,街坊就是一個小社區裡面生活的社群,是在一個共生的關係裡面的。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藝術家也需要知道沒有給街坊帶來什麼破壞,大家怎樣去共同生存,藝術家在這裡可以做藝術家的事情,街坊在社區可以做社區的事情,大家可以互相適應。
黃孫權:我特別想問阿峰,因為你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者,現在全球的狀況都差不多,因為地產的霸權,因為縉紳化,底層的人要麼生活得很苦,要麼他們就被迫離開他們原本的地方。你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或者像這樣的一個角色,怎麼想象去抵抗這些?
阿峰: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因為縉紳化不單只是政府和地產商的問題,它還是一般民眾的問題。香港的社區重建就老愛舉很美好的例子,讓一般人都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美好的社區。比如說重建觀塘的時候,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太古城,太古城就是香港很中產的社區,沒有什麼街道,管理很嚴密,你在裡面找不到一個茶餐廳,因為他們覺得茶餐廳比較低檔次,就是壞品味,縉紳化是用同樣的邏輯。但是另外一個方法是創造一個社區經濟,再具體一點來講就是從人的生活的價值、從人的生活裡創造,是平常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都可以參與到的。因為藝術其實可能只有他們參與、發表,自己去做,去表達一些看法,從他們自己內在的一些東西可以反省得到的。如果從人的生活來說,比如我們擺攤,我們上一代的人覺得家裡有些東西可以賣就會拿到街上去賣掉,可能節日的時候他們都會在街上賣一些小吃。但是十幾年來大家覺得小販佔用街道不好,不美觀,衛生有問題,政府就會來打壓。如果這些東西可以維持,你會維持他們生活的圈子,他們都會自發去擺,如果所有人都覺得上街擺攤沒有問題,其實就可以是一種比較真實的抵抗。
黃孫權:你們是不是有一個很有名老婆婆?
阿峰:Fred媽?對!
黃孫權:你要不要講一下她的故事?
阿峰:Fred媽很有趣,Fred媽我第一次見她是活化廳的第一個計畫,我們貼海報說舉報你的封關的歷史,然後她就跑進來。她是一個老婆婆,但是她做了很多慈善的事,她拿很多錢去大陸的山區建學校。她現在八十歲了,還會走路到山區裡面看建得怎麼樣,她還給我一大堆照片看。
黃孫權:她在大陸哪裡建學校?
阿峰:貴州,廣西啊!
黃孫權:行動力很強。她什麼星座啊?
阿峰:什麼星座啊?她好像是獅子座,有點白羊跟獅子座,不知道。但是最後她都沒有怎麼來,我們叫她Fred媽,因為她兒子Fred常常來,Fred在的時候她不來。但是Fred最後他不來,她就常常來。在活化廳開差不多兩年之後,當時內部人手有一些改變,我們想要走進社區多一點,所以這裡佈置上都有一點改變,然後她就每一天都來。最初可能她自己拿一些DVD來看。她的生活是這樣的,她每天花很多時間去研究中醫養生的事情,因為她想要研究一些辦法幫助大家抑制癌症之類的,她每天都在研究這些東西,也會教人家,也會去收一些人家可能不要的東西,比如說去醫院撿到一些沒有人要的,然後有時候就拿來活化廳。她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做這種事情,她把這些東西搬過來,然後有一些藝術家去幫她,因為她每天都來,所以這個合作變得很強。我們每一年的新年都會做計畫,她忽然之間就拿兩千塊錢來,說我們要做一個派飯團的活動。因為我們以前聖誕節、平安夜的時候做過一個叫「白色聖誕」的活動,就是派飯團,只做過一次,藝術家當成概念藝術去做,其實也做得蠻好。但Fred媽她搞錯了,她覺得新年也要做派飯團,所以她就不知道去哪裡找到人家捐給她兩千塊,她就要求我們一定要派飯團。然後就沒辦法,要幫她圓夢成真。但是我們沒有人手,因為新年可能有其他很多事,然後我們一發到網路上,計劃叫〈你幫我幫她〉,她就是Fred媽,然後一大堆人來,要替她實現這個願望。當天就有很多人在這裡做飯團,然後一起到外面去派。因為蒐集到網上有一個free cycling的group,叫OES free(音),然後他們很大一群人,有兩萬多人在Facebook上面,所以一發出去就有很大的回響。其實計畫概念是Fred媽媽發起的,然後大家替她實現出來。
最後很多計劃其實都是這種狀態,比如說活化區也是,最初Fred媽一下子很生氣,談起油麻地她就覺得油麻地現在的街道太冷清了,我們一定要去擺攤、去佔領街道。其實擺攤這個東西,我們想了很久,以前想過要做,但是我們找不到人來擺,就邀請藝術家來擺,藝術家平常又很忙。你搞不到哪個地點比較好,如果搞不好的話,會破壞到那邊的生態,你會引來很多警察,反而街坊會覺得你很麻煩,所以地點是一個問題。沒有人,地點,怎麼樣辦?但是Fred媽提的時候,就差不多都解決掉了,因為是街坊自己發動的。然後地點也是,因為已經有一段時間覺得可以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最初我們以為只有幾個街坊而已,怕沒有人來我們預備了很長時間。但是到去擺攤的時候,一下子整條街都滿了。
黃孫權: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街坊突然反過來要求藝術家一起合作。
阿峰:對,反而這些藝術家,因為我們真的以前想過要做差不多的事情,像這個free cycling,前幾年活化廳早期還不怎麼流行,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可以提出來,然後讓大家去做做,其實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街坊自己發動反而是更棒的。所以現在差不多每一個月都會做一次。
黃孫權:對,我知道Fred媽在德昌里擺。
阿峰:對,她在德昌里前面,東西是另外一個街坊送的,有很多,然後她擺攤,一天就可以賺一千多塊,比我們打工還好。
黃孫權:她生意很好。
阿峰:生意很好,一天可以賺一千多塊,所以現在不用我們組織了,她自己會。
黃孫權: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聽聽看阿峰你個人的看法,你這幾年都在跟社區、跟不同的藝術團體合作,香港有許多新媒體出現,你怎麼看待這些主流媒體跟那些小的團體?真正做社區組織的一些關係?
阿峰:我今天看一個漫畫,就是說現在香港社運怎樣升級,就是你最初看到Facebook上面的一個讚,然後在升級就是分享,再升級可能就是轉貼了,再升級就是改一改你的頭像,為什麼Facebook上大家都改了頭像了,這個社會還沒改變?香港現在一方面是你看到了很多新媒體出現,但還是有一個固定的人數,因為最近網路公投的時候,就看到我們有大概70萬人到80萬人,香港最厲害的網路媒體就是蘋果,蘋果每一天流量有一百萬,香港有七百萬人,其實這個參與人其實蠻固定的,所以媒體可不可以就是擴大其影響?是有一些新媒體出現,但是另一方面主流媒體越來越保守,抹黑,它偏向一個很明顯的立場,這也是香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但是比如說若TVB(香港無限電視台)可以改變,接觸到一個很大的觀眾群,它對於一般人的想法的影響力比較大。香港會說遍地開花,台灣好像反服貿之後也有遍地開花,但是遍地開花的同時,其實要聯繫到一些比較真實的生活的一些聯繫上面。比如說TVB主流媒體,大家習慣每天都看,這些是新媒體的人接觸不了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這種生活?一般生活上的媒體,我還聽說可以做到真的接觸到一些可能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會上網的這些一般的街坊,然後(瞭解)這一群街坊是怎樣想的,但是這一類的東西香港比較少人去做。我覺得新媒體,像我剛剛舉的那個笑話,新媒體會不會讓你從你的不滿變成行動?如果真的是跟你的生活很有聯繫的,再走多一步的可能性就比較大,所以這個反而更重要。但是香港真的很少有團體做得到,很少有團體做這個。
黃孫權:你不能只是改一下你的頭像,對不對?
阿峰:終極的是改你的圖像(笑)。
黃孫權:阿峰,你還知道香港有什麼社區報?
阿峰:有,剛剛這個就是,香港的社區報,我們都有收集起來。因為《活化報》出現之後,出現了很多社區報,應該不是我們影響他們的,但是就是忽然之間出現,其他人都做他們的社區報,不同類型的報,這樣的一張紙。這個是油麻地的,這個絕對是受《活化報》影響到的,也派油麻地,其他的社區報。我覺得社區報可以做,因為社區報成本很低,幾個朋友可以做。你接觸一個小的社區,因為香港現在剛剛起步的社區報全都很小,也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怎樣可以持續做。香港有很多很多小的社區報要發動一些東西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影響的。
這裡可以看到活化廳出版的個期活化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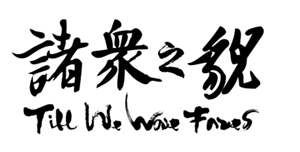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微信扫一扫,打赏作者吧~



發表迴響